
2020 03 18 “疫”线日记
2019年1月22日,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。下班途中我给爸妈打了电话,告诉他们第二天到家的时间。1月23号凌晨,当我看到朋友圈被“武汉离汉通道关闭”的消息刷屏时,我意识到今年我可能回不了家了。二十多年,这次是我第一次过年不能和家人团聚,虽有些孤独,但这就是我的工作。
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,就是退掉了回老家的火车票,给父母打了一个“请假”的电话,电话那头,爸妈让我注意防护,安心工作,但还是可以听出他们的一丝失落。带着爸妈的叮嘱,我开始了当记者后的第一场战役——战“疫”。

忘记危险,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画面
大年初一,我和钟玮在中南警务站蹲点,突然接到指挥中心调警的指令:辖区一位居民发高烧,还伴有昏迷的状况,指派民警找救护车,把发烧的居民送到医院。我们拿着摄像机,和民警一起出警,完整记录下民警救助的全过程。
因为任务太急,在没办法做好全身防护措施的情况下,我们就跟民警一起到了发热居民的家中。民警一边询问患者的身体情况,一边联系医院。二十分钟的时间,我一直处于近距离拍摄,直到医院的救护车到了现场,把患者抬上救护车后,看着救护车远离的背影,我才突然意识到,当时我们戴的是最普通的口罩。

(图为:大年初一胡爽和同事钟玮跟随民警转运发热病人)
那一刻,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害怕,回到单位准备做节目的时候,被晓薇姐大声“教训”了一顿,此时,我才感觉到有些后怕。按要求,我和钟玮一起,被要求回家进行隔离观察。
焦虑中,我接到出警民警的电话,送到医院的发热患者,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,当时一颗悬着的心,终于落了下来。当我手握摄像机的时候,根本就没想到有什么危险,只想把现场完整地记录下来。
重回岗位,离“危险”更近一点
在家观察了一天,身体没有任何不适,我申请重回工作岗位。我想,如果这次不到前线,一定会留下遗憾。
2月21日,是我第一次到方舱医院采访。说实话,嘴上说不怕,心里还是会犯嘀咕。防护流程比较复杂,我花了将近四十分钟,才换上了厚厚的防护服,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还没穿一会儿,已经明显感觉大脑缺氧,开始呼吸困难,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,穿着防护服工作是有多么的不容易。

(图为: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,医疗队员帮胡爽检查防护服)
我的搭档,是胆大的晓薇姐。洪水、汶川地震、“东方之星”沉船现场,都有她逆行的身影,所以我跟着她,心里自然也会踏实许多。

(图为:“生死搭档”胡爽和张晓薇)
那天采访的是一对父子,儿子王桓峰是重案队的刑警,一直在方舱医院值勤,二十多天没见生病的父亲。再见父亲时,却是在王桓峰值勤的方舱医院。父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你是一名党员,做好你自己的事情。”
虽然我早就写下了入党申请书,也参加过积极分子学习班,但是,对党员的理解,更多的是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,总感觉他们离我很远。只是当那天采访到王恒峰父亲时,我第一次感觉到,其实英雄就在我身边。王恒峰的父亲说:“我是一名老党员,在方舱里既是一名患者,也是一名志愿者。儿子就是一个执勤的公安干警。我们要分清楚各自的职责,身处这个岗位,应该把国家利益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。即使有风险,那也是要去承担。”
而我的职责,就是记录下抗击疫情阻击战中的感动。

(图为:2月21日在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采访民警王桓峰的父亲王宁)
“迷你ICU”的四次眼泪
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三病区内,有个“迷你ICU”,里面住着三位危重病人,患者小飞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“迷你ICU”,是红区中的红区。
在进重症监护病房之前,我已经去了好几次方舱医院了,多少有点心理准备。当我和晓薇姐被中国医大盛京医院ICU的主任贾佳问到“你们进过红区吗,会不会穿防护服,出来会不会脱防护服”的时候,我们面面相觑,竟不知道该不该说“会”。贾佳,也是这个“迷你ICU”中患者小飞的主治医生,东北人性格豪爽,说话嗓门也大。他的“唠叨”,让原本不那么紧张的我,开始紧张起来,心越跳越快。

(图为: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病房,穿戴完毕准备进污染区)
进入“迷你ICU”,第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飞。医护人员无暇顾及自身的安危,都在忙着帮他换药、吸痰。

(图为:援鄂医疗队员正在给患者小飞换药、吸痰,记者胡爽现场拍摄)
不知不觉,我在病房待了也快两个小时了,突然觉得自己眼前发黑,身体开始晃动,呼吸也有些跟不上来。但那个时候,我们正在采访贾佳主任,我低着头,咬着牙,努力举着OSMO(注:摄影器材)不让它晃动,坚持到最后。采访一结束,晓薇姐一扭头,看我已经有些站不稳,一把把我扶到过道上透透气。
我隐约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对话。
——护士说:“给他吸点氧。”
——医生说:“不行,吸氧就会暴露。”
——晓薇姐说:“送他出去吧。”
——医生说:“这也不行,脱防护服时间长,有危险。”
晓薇问我要不要出去,我用劲摆摆手说:“没关系,休息一下就好。”直到完成拍摄工作,晓薇对我说:“你那一倒,把我的魂都吓没了。”
其实当时,我根本就没有想到“危险”这两个字,只想把现场完整地记录下来。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,可能是那些白衣天使不放弃的精神,可能是患者面对疫情时的乐观和感恩,这一切,都让我充满了力量。

(图为:采访中感到缺氧,被扶到窗边透气)
不知不觉,我们在ICU已经超过五个小时。最后,我们是被贾主任“赶”出来的。从医院出来的时候,我对晓薇姐说:“今天,我流了四次眼泪。”
第一次眼泪,是为病情好转的重症患者朱阿姨流的。她哭着说:“是医疗队的医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”她说,能够从全国各地调来医生,只有中国才能办得到,祖国真的太强大了。
第二次眼泪,是为“方舱歌王”李叔的一曲《我的祖国》而流。李叔跟着电视节目越唱越带劲,歌声里全是他的自豪感。慢慢地,他的声音哽咽了,他说:“我从方舱医院转到了这里,也从方舱医院唱到了这里。虽然每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,但是没关系,我一定会好的。在中国,我特别安心。爱伟大的祖国,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。”

(图为:医生给患者小飞换药)
第三次眼泪,是看到小飞的妻子和他微信视频。电话那头的妻子非常乐观地对小飞说:“你肯定会好的,我们等你回来。你一定要坚强,等你出院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小飞虽然不能说话,从他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他对生命的渴望。
第四次眼泪,为一名87岁的老奶奶。她说自己是一个老党员,相信党。当她挥着手对救了自己命的医护人员们说“再见”的时候,我真切地感受到:希望就在前方了!
回忆这段特殊的日子,受访者的一个表情,一句话,这些场景经常在我眼前浮现。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,感谢这次“大考”,让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。
监制:郭小容
编审:吴博军 郭晓勇
作者:胡爽
编辑:刘蕊俊
(责任编辑 马张驰)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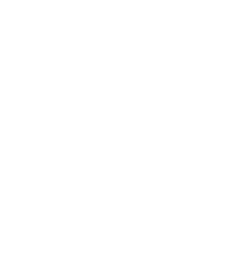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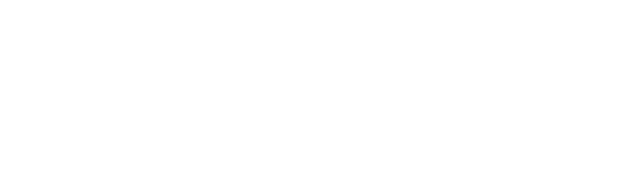

暂无评论,快来抢沙发~